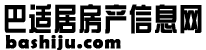房产证被偷了怎么办:房产证被偷了怎么办会怎样
行为人将房本偷走后,又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并出卖给第三人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呢?本文将通过一则案例分析此类行为

行为人将房本偷走后,又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并出卖给第三人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呢?本文将通过一则案例分析此类行为的定性本公众号在2016年5月4日推送的“【窃取风云之一】房屋能被盗窃?”也对这类行为的定性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您对这一问题有何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或来稿参与讨论对于在本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的原创稿件,将结合阅读量酌情给予奖励,湖南省刑事法治研究会每年还将对原创文章进行评奖并予以不同等级的奖励期待您的来稿!投稿邮箱:hnsxsfzyjh@126.com。
案情简介陈某与崔某于2008年离婚后仍时常来往,户口也未分开2013年底,陈某自购商品房一套,未入住崔某得知后偷偷用假房产证换走真证,并找到长相酷似前妻的颜某,冒名补办了陈某的身份证,二人又领取了结婚证。
之后,颜某继续假冒陈某,凭借新结婚证、老户口本、房产证及冒领的身份证将陈某的房屋过户给崔某2014年2月,崔某与邵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140万元市场价将房屋过户给邵某陈某缴纳物业费时,发现户名被更换,遂报案。
争议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崔某和颜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崔某出卖房屋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又在陈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了秘密窃取他人房产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第二种观点认为,房屋不能成为盗窃对象,崔某和颜某是通过欺骗行为取得了对房屋的产权,被害人是陈某,被骗人是房屋管理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因此本案构成诈骗罪,属于三角诈骗。
本文观点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认为崔某和颜某成立盗窃罪,理由如下:一、本案盗窃的对象不是房屋,而是陈某对房屋的产权我国刑法没有像德日刑法那样严格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而是在侵犯财产罪这一章中使用了“财物”这一概念。
而是否能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盗窃罪中的“财物”,在刑法理论上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有些学者主张在理解我国刑法中的“财物”时,可以参照德日刑法的相关规定,抢劫、诈骗、敲诈勒索等罪的对象可以是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而盗窃罪的对象只能是狭义财物。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财物应当包括财产性利益,盗窃罪的对象既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财产性利益第一,由于我国刑法的规定不同与德日刑法的规定,在此问题上就不能照搬德国、日本等国的做法我国刑法没有明确区分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也未将二者作为并列概念使用,因此在理解“财物”这一概念时,就不能想当然地参照德日刑法将财产性利益排除在外。
从解释论上来说,当两个概念并列规定一个法条中时,其中的一个概念不可能包括另一个概念,但当法条仅使用其中一个概念时,就完全可能使这个概念的外延包括另一概念的内容例如司法解释认为刑法第227条第一款规定的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中的“伪造”包括变造。
第二,在我国,盗窃罪的成立以数额较大为起点,对单纯盗窃财产性利益的凭证的行为,不可能以凭证本身的价值认定为盗窃罪,因而不利于保护财产性利益另一方面,许多财产性利益已经没有书面凭证,只有电子凭证(如国库券)。
即使将盗窃财产凭证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结合现实来考虑,许多财产性利益与狭义的财物已经没有实质区别,如果将财产性利益排除在盗窃罪的对象之外,则不仅难以保护财产法益,而且会造成处罚不协调的局面。
最后,将盗窃罪中的“财物”解释为财产性利益并不属于类推解释,不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某种解释是否违背罪行法定原则,在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对一个行为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
而盗窃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与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在法益侵害性上是基本一致的,具有处罚的必要性,因此对“财物”一词有做扩大解释的必要而且因为盗窃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本身具有明显的法益侵害性,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所以将盗窃罪中的“财物”解释为财产性利益,并没有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范畴。
如果认为盗窃罪中的“财物”不包括财产性利益,那么将他人的存款转移到自己的存折后,在还没有现金化的期间,通过自动付款缴纳电话、水电等费用,由于行为人没有取得现金,仅取得了财产性利益,就不能认定为盗窃罪,这显然不妥当。
当然,并非所有财产性利益都能作为盗窃罪的对象张明楷教授认为,作为盗窃罪对象的财物,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具备管理可能性,这是相对于被害人而言的,如果被害人根本不可能管理,我们就不能说被害人占有了某种财物,因而也不能认定其丧失了某种财物。
而且,盗窃罪表现为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所以只有被害人具有管理可能性(可以占有)的东西,才可能成为财物第二,具有转移可能性,这是相对于行为人而言的,如果行为人不可能转移被害人管理的财物,就不可能盗窃被害人的财物;第三,具有价值性,这是相对于保护法益而言,如果一种对象没有任何价值,就不值得刑法保护。
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对财产犯罪案件的分析,首先要确定被害人,然后要确定被害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的具体内容(即行为对象与侵害结果的具体内容,是有体物遭受损失,还是财产性利益遭受损失,是何种财产性利益遭受损失),接下来要判断造成具体财产损失的行为是什么性质,该行为符合何种犯罪的构成要件。
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将结果抽象化在盗卖不动产的案件中,不能简单认为不动产就是犯罪对象,而是要分清楚行为所侵害的是不动产本身(有体物),还是不动产的产权或者其他利益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中的房屋具有不可移动性和不可藏匿性,其所有权的转移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基于此不动产盗窃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而在实践中不可能出现。
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但本案中盗窃的对象并非不动产,而是陈某对其房屋的产权根据上文所述,盗窃罪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而房屋产权作为财产性利益符合作为盗窃罪对象的财物的是三个特征首先,房屋的产权是具备管理可能性的,房屋的所有人要到房屋登记机构办理房屋登记,取得房屋权属证书,房屋的所有权人可以自由的占有、处分、使用、收益自己的房产。
其次,房屋的产权也具有转移的可能性,本案中颜某和崔某拿着冒名补办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和房产证,到房管局办理转移登记,将陈某名下的不动产转移到了崔某的名下,实现了房屋产权的转移最后,房屋的产权当然具有价值性。
但是房屋产权的价值性虽然容易认定,但认定房本的价值性却存在一定问题房本虽然可以证明所有人对房屋的所有权,但一方面,房本并非房主对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凭证,房屋所有人将房本遗失的,仍然可以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内容来证明自己的所有权。
另一方面,普通盗窃行为构成盗窃罪的,以数额较大为前提,没有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多次盗窃等情节的,难以认定对房本本身的盗窃罪因此,本案盗窃罪的对象既不是房屋,也不是房本,而是陈某对房屋的产权二、崔某和颜某实施的是盗窃行为
根据上文所述,崔某单纯将房本偷走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但在本案中,由于崔某偷走房本后与颜某实施了一系列的行为将陈某对房屋的产权转移到了自己名下,因此崔某偷走房本的行为具有刑法评价的意义笔者认为,在评价财产犯罪中的“财物”(狭义财物)时,不仅要看到有体物本身,也要看到有体物背后蕴含的经济价值。
以日本刑法为例,日本刑法虽然没有将数额较大规定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但是行为人盗取价值微薄的财物(如几张白纸)时,刑法理论和审判实践要么以价值微薄的财物不属于刑法上的财物为由,否认该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要么虽然认为该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但认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因而不以盗窃罪论处。
但是倘若行为人使用公司的复印纸复印了商业秘密之后,将载有商业秘密的这张纸拿到公司以外,则会被认定为盗窃罪(由于日本刑法仅将有体物作为盗窃罪的对象,所以单纯盗窃商业秘密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显然,在这样的场合,实际上是因为行为人非法占有了财物的经济价值,才以盗窃罪论处。
日本还有判决明确指出,情报载体的财物性,不仅就载体的素材进行判断,而应综合情报与载体进行判断,财物的价值主要是情报的价值由此可见,在日本审判实践中,对于行为人窃取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纸张等载体时,虽然只能认定为对纸张等有体物的盗窃,但实际上考虑的是纸张所记载的商业秘密等情报的经济价值。
虽然不能将日本刑法和审判实践直接照搬到我国来适用,但参照其理论来认定我国财产罪中的狭义财物是很有必要的结合本案来看,房本的价值绝对不仅限于一片薄薄的纸,其背后是蕴藏着经济价值的虽然房屋权属证书不是证明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凭证,行为人偷走房本的,也不能证明其事实上实现了对房屋本身或房屋产权的占有,但不能据此否定房本背后的经济价值。
本案中如果没有崔某以假房本换取陈某真房本的行为,即使颜某冒名办理了身份证,也不能实现房屋产权的转移,因此应当对崔某转移房本的行为进行刑法上的评价笔者认为,崔某盗窃房本的行为是盗窃罪的手段行为,此时对房屋产权的侵害还没有紧迫、现实的危险性,是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属于盗窃罪的预备行为,这就相当于为诈骗公私财物而伪造文书的,伪造文书的行为本身不可能使财产处于紧迫的危险之中,属于预备行为,而开始使用所伪造的文书实施欺诈行为时,才是诈骗罪的着手。
值得注意的是,将崔某以假房本换真房本的行为评价为盗窃预备,是结合本案的案情做出的分析,在实践中不能一律将盗窃房本的行为评价为盗窃罪的预备,也就是说没有崔某之后伙同颜某到房管局办理转移登记的行为,是难以认定崔某盗窃的对象是房屋的产权,而非房本,难以认定崔某偷走房本的行为是盗窃罪的预备行为。
本案中颜某冒充陈某,带着冒名补办的身份证、结婚证、老户口本、房产证到房屋管理登记机构申请办理转移登记的行为,对陈某的房屋的产权构成了紧迫、现实的危险性,构成了盗窃罪的“着手”,而当房屋管理登记机构受理了二人的转移登记,将不动产登记簿和房屋产权证书上的所有人变更为崔某时,房屋产权事实上由转移给了崔某,盗窃罪最终既遂。
由于房屋产权的特殊属性,国家房屋登记管理机构对房屋进行严格的登记和管理制度,这就决定了盗窃房屋产权的行为与盗窃动产的行为在转移占有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本案中崔某和颜某在违背陈某的意志下转移其所占有的房屋的产权,由于房屋登记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处分服务房屋产权的权限,二人的欺骗行为难以认定为诈骗罪,所以本案构成盗窃罪。
三、房管所的工作人员不具有处分房屋的权限或地位,本案不构成三角诈骗第二种观点主张本案构成三角诈骗,但这一观点的最大缺陷在于难以认定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具有处分房屋的权限或地位在三角诈骗中,被骗人(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不具有同一性,但被骗人事实上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
例如丙是乙的家庭保姆,乙不在家时,行为人甲前往乙家欺骗保姆丙说:“乙让我来把他的西服拿到我们公司干洗,我是来取西服的”丙信以为真,甲从丙手中得到西服后逃走,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可知,保姆丙是具有处分主人乙西服的权限或地位的。
判断受骗人事实上是否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时,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以其事实上是否得到了被害人的概括性授权为基准;至于是否得到了被害人的概括性授权,则应根据受骗人是否属于被害人阵营、是否是财物的占有者或者辅助占有者、其转移财产的行为外表上(排除被骗的因素)是否得到社会一般观念的认可、受骗人是否经常为被害人转移财产等因素来进行判断。
在本案中,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只是对变更登记的材料进行纯粹的形式审查,其并不会实质地考察房屋产权变更是否合法,也无权裁判房屋产权的归属房管局是中立机构,并非陈某对房屋产权的占有人或者占有辅助人,其工作人员在没有陈某授权的情况下进行转移登记的行为也并没有得到社会一般观念的认可。
事实上房屋登记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只是根据申请人的授权来办理转移变更的事项,而本案中转移登记的行为显然没有经过陈某单独的授权,是在完全违背陈某的意志下“秘密”进行的认定房管局或其工作人员具有处分房屋产权的权限或地位,事实上会扩大公权力行使的范围,不利于私人财产的保护。
因此,登记机关单纯的登记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意义上的财产处分,也就不能以三角诈骗追究崔某和颜某的刑事责任其次,笔者认为不能根据崔某和颜某二人具有欺骗房管局工作人员的行为而直接得出二人成立诈骗罪的结论事实上,盗窃罪并不排斥欺骗行为的存在,例如甲欺骗超市老板乙称乙的儿子丙在路上出了车祸,乙急忙跑出去,临走前让甲帮自己看店,甲趁乙走后将超市里的钱洗劫一空,此案中虽然甲具有欺骗行为,乙也因为甲的欺骗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但甲让乙看店的行为并没有将店里的财物处分给甲的意思,因此甲成立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
所以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键并不在于行为人有没有实施欺骗行为,而是行为人是“秘密窃取”财物还是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处分而取得财物本案中崔某和颜某是违背陈某的意志下秘密窃取了房屋产权,而非基于房屋管理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有瑕疵的处分取得陈某对房屋的产权,因而构成盗窃罪。
结语综上所述,崔某和颜某对陈某的房屋产权成立盗窃罪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崔某将房屋出卖给邵某并办理过户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呢?虽然《物权法》目前没有明确规定盗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在民法上,尽管解释的路径有差异,但大多数意见还是肯定在冒名处分的情形下,善意第三人仍可终局性地取得所有权,除非有可归责于善。
意第三人的事由,比如善意第三人疏于审查等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1年3月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因此,笔者认为善意第三人邵某可以最终取得本案中房屋的所有权,崔某对邵某不成立诈骗罪参考文献略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湖南省刑事法治研究会编辑:李豆豆案件来源:中国法院报往期精彩:【窃取风云之一】房屋能被盗窃?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